2019年清明刚过,巷口的梧桐树抽着新芽。我攥着皱巴巴的简历,第三次推开「山间」咖啡馆的玻璃门。水汽在镜片上凝成白雾的瞬间,吧台后面传来带笑的声音:“今天没带伞?”
郑儿把毛巾叠成规整的方形推过来,深棕围裙上别着银底黑字的「首席咖啡师」胸牌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总把头发扎成松散丸子头的姑娘,是西南赛区咖啡冲煮大赛的冠军。
| 我的初始认知 | 实际工作要求 |
| 咖啡师=操作机器 | 掌握27种冲煮手法 |
| 拉花最重要 | 水质检测优先 |
| 记住配方就行 | 每天校准磨豆机 |
入职第三天,我自信满满地给客人做美式。郑儿突然按住我正要倒掉的咖啡渣:“豆子磨粗了0.5格,水温低了2度——你闻,坚果味都没出来。”
那个梅雨季,储藏室变成了实验室。郑儿把不同产地的豆子装进贴满标签的试管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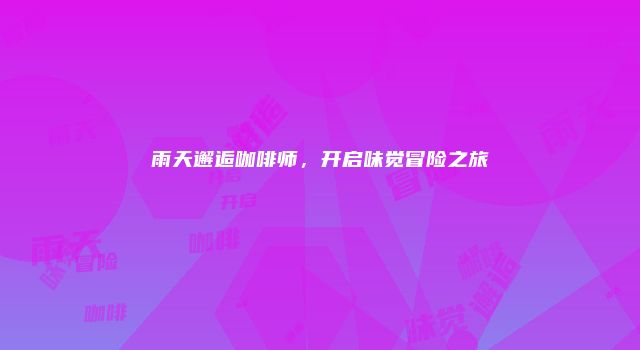
| 云南小粒种 | 雨后青苔/山核桃/尾段微涩 |
| 肯尼亚AA | 黑加仑汁/红酒醋/明亮酸质 |
| 苏门答腊曼特宁 | 潮湿木头/黑巧克力/奶油质地 |
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独立完成杯测的情景。郑儿蒙着眼啜吸时,喉结紧张地滑动——直到她竖起大拇指:“这个危地马拉的蜜处理,有成熟木瓜的甜感。”
连续37天,打奶泡的尖啸声在凌晨回荡。郑儿独创的「三段式融合法」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:
当我终于拉出对称的天鹅时,常来买早餐的老画家掏出速写本:“小姑娘,这个画面值一杯咖啡。”
台风登陆那晚,有位西装革履的客人冒雨前来。他盯着我胸前的实习徽章迟疑片刻,还是点了杯手冲。
郑儿突然从后厨转出来,往我手里塞了支温度计:“记得《咖啡品鉴学》里说的酵素反应吗?”玻璃门外暴雨如注,我们却像在进行某种神圣仪式。
客人举着杯子怔了许久,最后留下张便签:「这是我喝过最温暖的巴拿马瑰夏」。
现在走进「山间」的人常会看见:扎丸子头的女咖啡师倚着料理台,看年轻学徒给客人讲解咖啡豆的日晒过程。阳光穿过玻璃斜斜切进来,把墙上的SCA证书镀成淡金色。
上个月市集活动,当我用冰滴壶做创意特调时,郑儿默默把她的冠军手冲套装摆在了我的操作台旁边。咖啡的香气混着初夏晚风,在人群的惊叹声里轻轻打了个旋。